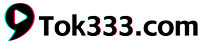责任编辑: hongyusu.com
知美术馆位于四川省新津老君山脚下,美术馆四面环水,而水流是道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有无相生”的问题,当中的重点并非古代西方哲学家们如巴门尼德或亚里士多德般一直围绕着“存有”和“虚无”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探索。老子关心的更多是“有”和“无”之间的“相生”,正如法国生命哲学家柏格森所谓的“生成”(devenir)和绵延(durée)。但为什么人总以为“存有”的“消失”就是“虚无”?这是因为人的意识中不知道构成事物消失的并非虚无,而是德勒兹哲学中的“拟像”(simulacre)。
正如古希腊画家宙克西斯(Zeuxis)与帕尔哈希奥斯(Parrhasius)比赛的故事。传说二人都是古希腊的著名画家,画什么都很逼真,他们相约比赛谁的画更逼真。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公开评审前用一块布遮挡着。宙克西斯先揭开自己的挡布,他的作品所呈现的是一串葡萄,这时一只麻雀飞来啄向那葡萄,评审们都很惊讶这张画的逼真程度。然而这时帕尔哈希奥斯却不慌不忙、也不揭开自己作品的挡布。此时宙克斯情急下去揭开挡布,却在揭开那一刻突然说“我输了”——原来帕尔哈希奥所画的正是那块挡布。
这块布就是德勒兹所谓的拟像,它并不以“存有”与“虚无”来呈现自己,反而它只是“有或无”的中间状态,或者简单说它就是“或”本身。这个作为“或”的拟像成为了一切事物消失的起点。就如同以上故事一样,《消失的展览》不是关于作品的“有”或“无”——画出来的挡布正是作品从有(宙克西斯本以为布的背后“有”作品)到无(原来此作品就在他眼前而他却完全不知)过渡的消失状态。因此,拟像不是一个具象,它只是让事物消失的一种能力而已,或者一种事物“生成”和“绵延”的过程,而老子所言的“相生”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
受道家哲学启发的展出《消失的展览》,希望能呼应隈研吾的理念“消失的建筑”:“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我始终关注于研究如何让建筑‘消失’。我真心渴望建造的是一座能够完全消失在周围环境中的建筑”。由此出发,《消失的展览》以当代艺术的形式,与隈研吾的“建筑之隐”展开对话:每一件参展作品都能够与知美术馆的建筑、与隈研吾的建筑理念和建筑特点发生关系。艺术与建筑,在这个主题下彼此重新激活。
这是一个规模小、作品数量少,但作品的内涵与美术馆建筑之间张力很大的展览。展览以隈研吾的建筑和设计理念为核心,邀请刘国强、熊佳翔、张琪凯三位当代艺术家参加展览。希望通过他们的作品,去理解隈研吾的建筑理念,去重新观看、体验知美术馆的空间,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人与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美术馆就是在建构一种让你能够通过你的思考系统、生成新知识的能力”,中央美术学院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曾在接受访谈时提到:“未来美术馆的展览应该是创造一种新的体验,在体验当中认知,在认知当中得到再认知,然后推动创造性思维来生成新知识。”在文献部分,以知美术馆为核心,首次呈现了隈研吾在设计这座美术馆时的珍贵历史资料。
隈研吾的“隐”,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而《消失的展览》则期待能实现一场“看不到”作品的展览,一个“空”的空间。每件作品都能与知美术馆的建筑空间高度融合——哪怕作品就在眼前,可能观者也没有意识到这就是作品——而通过这些作品,观众又能重新去品味隈研吾的建筑设计理念,重新去感受知美术馆的整体空间,获得一种新的观展角度和观展体验。
 作品《柱子》
作品《柱子》 知美术馆的三层展厅,是一个没有柱子的空间。看上去一片空旷的展厅正中间,突然出现了一根柱子——观众可能意识不到这是一件作品,但其实这是90后艺术家熊佳翔为本次展览创作的作品《柱子》。
“柱子一般是给人支撑物的感觉。从这个为出发点,展开了我对于支撑物的思考,柱子可以是一个形象,结构,也可以是一个人的名字。”在准备阶段的讨论中,熊佳翔对知美术馆三层顶部的一个正方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我看到那个方块时,我分明看到了一个身体的‘脐’,它处于一个半遮蔽的状态,既闭合又打开”。其实这个正方形是放置可升降投影仪的地方,平日里这个空间确实是美术馆的一个隐藏空间。选择把“柱子”立在这里,其实连通了美术馆的隐藏空间——让消失的空间被看见,而可见的这根“柱子”却又是可以消失的。就像熊佳翔所希望的“柱子的存在会把这个建筑的结构、装饰、设备这三者的关系模糊和彻底搅乱。”
从观念上,《柱子》呼应了隈研吾对于建筑“隐”的概念。而从材料上,熊佳翔认为:“织物是建筑的原型,编织的方式也是建筑的方式,从编绳到布料再到建筑结构,布与建筑是同类。”《柱子》同时也呼应了隈研吾建筑中“举重若轻”的特点——他曾经提到“减轻大块平面的重量感是我的建筑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莲屋”、还是“小松精炼纤维研究所”,隈研吾都通过精巧的设计使原本厚重的材料变成视觉上的轻盈。
而回到《消失的展览》,位于知美术馆三层展厅视觉中心的这根柱子,其实是用布、按照服装制作的工艺手工缝制而成的。柔软的柱子好像硬性地切割了整个空间,它的关键词是空心与贫瘠,这带给人意外之感。这与柱子的关键词--“承受重量”之间构成了巨大的反差。撩开布,人就可以进入到“柱子”内部,或径直穿越过去——空间之中并不存在“柱子”。在这里,作品中隐含的与人的身体的内外互动性被彻底打开:人可以在建筑之内,又可以在建筑之外。柱子本来的作用是支撑建筑,但在《消失的展览》中,柱子却不是用来支撑、分割空间,可能是连结空间,从而引人去思考:空心的“柱子”是在描述一种怎样的存在状态?在表达着怎样的一种情绪?如何支撑一个空间?消失的是人还是展览?它在这里的原因又是什么?
 作品《X(折叠系列)#1 》
作品《X(折叠系列)#1 》 “不论建筑还是生物,都因流动而活着”。刘国强本次参展作品《X(折叠系列)#1 》(简称《X》),带给人普通之物的不寻常之处,也带人去重新体会隈研吾提出的“建筑物是无限延伸的时空连续体的一部分”。在知美术馆的三层,左边墙面的材质是黑色大理石,右边墙面则选用了呈灰白色的木丝水泥板(Wood wool cement board)材质(是由水泥作为交联剂,木丝作为纤维增强材料,压制而成的板材),表面具有原始粗旷的丝状纹理。视线从“柱子”的边缘滑过,远方的灰白色墙面上似乎隐隐有块白色,走近后才会发现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但纸的正中被切割的部分被旋转、折叠,好像一件三维的“纸雕塑”。
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刘国强,创作上一直注重观念性与实验性,从创作角度,他希望“把最正常的变为最不正常的”。当凝视《X》时,隐约感受到一种固态之中的流动性,缓缓从纸面中跃出。就像面对隈研吾设计的Chokkura广场时,那些由普通的大谷石构成的结构墙,好像波浪一样层层涌来。X代表着无限与未知,这件作品在方寸之间让人感受到时空的巧妙转换。而从材质上,纸的纤维消逝在凹凸不平的木丝水泥纤维之中。联想到位于韩国安养市、由隈研吾设计的“纸蛇”——“日本折纸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通过一张薄纸的折叠来创造力量,不同的折叠方法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力量”。
《柱子》与《X》两件作品,彼此之间形成了某种基于对话关系上的隐匿状态,无论是从颜色上,还是从作品自身的建筑性和结构性上,好像一个彼此沉默的空间剧场。
在美术馆的二层,在玻璃幕墙构成的三角夹角处,“隐藏”着张琪凯的作品《脆弱之间二号》。这两个看似来自海洋亦或外太空的生物,手拉手站立着。夹角是对建筑物起支撑作用的;而对于这件作品,起到重要支撑作用的是这两个物体“手拉手”的部分,也就是说,第三只脚,不是独立的,而是由两个物体交融的部分共同构成的,这种支撑,是隐性的,却又是最重要的。面对“脆弱之间”,不禁让人联想到建筑、人、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及其脆弱的。
 作品《脆弱之间二号》
作品《脆弱之间二号》 “洞穴”概念是隈研吾一直贯穿着在思考的核心之一,在他的众多建筑作品中,“洞穴”概念被他反复的再审视。无论是那珂川町马头广重美术馆,还是知美术馆,每一个项目的正中间都有一个巨大的“洞穴空间”。童年时一次偶然进入洞穴的玩耍经历,对隈研吾之后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时我会感觉到自己其实并不是在做一个建筑,而是在思考一个洞穴般的东西”。《消失的展览》也首次激活了知美术馆地下一层的X空间,它作为美术馆整体空间的一部分被长期的“遮蔽”。这个地下空间结构丰富——从侧面进入知美术馆的地下一层,一条狭长的黑色通道激发着向前探索的欲望;而通道的左右又连结着什么?通道右侧,进入一个全黑的“洞穴”之中,隐约看到一块石头与一片白沙——张琪凯的作品“石骨”被放置在这里,一块由无数小木棍支撑起来的石头,在洞穴深处形成了一个力的场域。
“或许张琪凯对自然物的使用受到日本‘物派’(MONO-HA)艺术的影响”,在麓山美术馆艺术总监田萌看来,“他和‘物派’艺术一样,注重自然物与其外部性所共同构成的现场,但与其不同的是,他强调了物体之间的力学关系。或者说,他通过某种力学关系将我们的目光从自然物本身进一步引向了隐含于物体的不同属性。没有什么物体是孤立存在的,一切都在关系中。”
 作品《石骨》
作品《石骨》 无论是“洞穴”之中的“石骨”,还是黑色通道尽头的豁然开朗,对于隈研吾而言,“洞穴是连接着左右两侧事物的媒介,使得左右两侧的空间发生对话。它不像洞窟那样封闭,而是在唤起公共性的同时,光明正大地展现出来”。洞穴应该是先充满了生物般的柔和,再将人和人之间牵连起来的场所。
消失的建筑,消失的展览,消失的关系。那些看不见的,比看的见的,重要的多。
文章编辑: hongyusu.com